1986年,黃建新完成了電影《錯位》:一個原本為應付無聊工作而被創造出的“機器人”,隨著時間推移擁有了自己的個性,甚至插手“主人”的生活試圖取而代之……在30多年之前選擇用影像探討尚未被廣泛認知的人工智能概念,他的這次創作有著可以被定義為先鋒的時代精神。
有趣的是,當時間來到2023年,人工智能早已不再是某種前瞻性的想象,而是全面進入并影響著我們的世界。
《錯位》也在此時完成了它最恰逢其時的“歸位”。與大部分比這部電影更年輕的觀眾進行交流,讓黃建新感覺很奇妙,“我其實挺緊張的,隨著年紀增長,人肯定會變得有點遲鈍,但我不想停下來,還是想往前走。” 電影自然也不例外。本屆平遙國際電影展,“AI”通過各種方式加入到創作與討論之中:由人工智能繪制的影展海報;開幕式上,費穆、卓別林等“大師”在科技加持下“親口”向年輕觀眾闡述創作理念;電影人圍繞AI接下來會怎樣改變行業提出各自明確的觀點……
“Keep Rolling”,不停向前。這也是黃建新這場大師班確定下的核心主題。除了由展映影片《錯位》引出過去先鋒的創作,如今成功變換更多身份,成為行業“金牌監制”的黃建新也還暢談了關于當下行業、市場發展模式的理解,以及作為最早一批關注人工智能的創作者,對于AI與電影未來交互的想象。
沿著過去—現在—未來這條“不停向前”時間坐標,我們整理了黃建新關于探索的成功與失敗、新主流類型創作,AI將如何改變電影的思考與答案。
(以下內容根據黃建新自述整理)
過去
寧肯在探索中失敗,不在經驗中茍活
《錯位》在疫情的3年里,又一次在網絡上被“炒”起來。包括身邊的朋友也問我,你那時候怎么會有一個AI的概念?我說沒有,我拍的是荒誕喜劇。之后有人把我送審報告里填的內容翻了出來,說“你自己寫了某某某做了一個智能機器人,替他開會”,其實我都忘了。
在這之前,我本來準備拍一個故事是講住房問題的。后來我跟很好的編劇朋友一起討論了一個多星期,又寫了兩個星期,《錯位》就準備開拍了,所以其實這個電影是一個偶合成功的電影。
我是個從小腦子里就愛亂想的人,拍《錯位》的時候,我自然想做個自己喜歡的東西。工程我不懂,比如像美國科幻片拆開無數的電路等等這些,我們做不了,就想用荒誕性跳過科技邏輯,只寫我們實際的靈魂和真實的人,用最真實部分和最虛假的部分對立,表現出人格分裂或者被異化的矛盾中的故事。

當時我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,口號是“寧肯在探索中失敗,不在經驗中茍活”,就貼在我們辦公室里。我們那一代人,對生存和工作有一種本能的珍貴,拿到一個工作不管你干啥,先把它干好,否則自己養活不了自己。
第五代導演在那時受到了國際影評人的注意。那時候參加國際電影節最大的受益是不停的看電影,這個電影節結束就買經濟艙機票飛到下一個再去看,不停的看,不停的交流,不停的學習。大家是互相促進的,有時候你的開悟不是系統學了多少,而是某一句話激活了你多少年的積累。電影就是做交流產品,而我大概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成長起來。
現在
不夠藝術家的位置,我是一個匠人
我是拍文藝片出來的,我發現文藝片的導演們容易批評商業片的導演,但商業片的導演很少批評文藝片的導演。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是兩個系統的東西,正因為這兩個系統同時存在,電影才豐富多彩。
我后來一直想做中國的市場電影,這么多年我覺得還是有了一點點成績,這不是我個人的,而是大家慢慢接受了這個觀點,共同努力。
最早其實沒有人想要我這個監制。監制應該起到什么作用?第一任務是保護導演,你要建立一堵墻,現在電影越來越多的多方投資,有一些是專業投資公司,很多不是,如果每個人都去跟導演談想法,那導演還要拍戲嗎?所以監制要擋在前面。
第二是規劃好從頭到尾電影流程,使導演們永遠在他的位置上。我們現在的導演有點壓力太大,啥都得管。單純性是藝術最寶貴心理動機,所以制片團隊、監制都要完成你的第一任務,就是保護創作,而不是干涉。

這么多年的經驗積累下來,我為什么還是喜歡做監制這件事?我一直認為我不夠藝術家的位置,但我是一個很好的匠人,我很擅長學東西。
轉到商業的方向,我們發現電影最容易讓觀眾接受的形態是感性形態。做電影這個很重要,你的情節段落是不是能夠從感性上激活觀眾心底(的情感)很重要,我們還是從世界電影學到了很多東西。
比如我們復盤過《長津湖》。我是編劇之一,我們有很多問題,它倉促、幾個導演拍、風格銜接難度很大。但是《長津湖》解決了一個戰爭片一直沒能解決的問題,就是“追隨”。
觀眾在電影院里看電影,他的心要追隨某個東西而行,這點大家一定要記住。《長津湖》寫了第九兵團里面的一個連的死亡史。開頭陳凱歌導演拍的部分就需要觀眾喜歡上這批人,觀眾喜歡,他們就會追隨這六個人,直到最后犧牲只活下來一個。人物也是商業電影核心,要有更通俗的情感,把大眾的共鳴寫進我們的角色,放到大的背景里去跟隨。

藝術電影有時候感性的點比較高,大部分人跟不上。你不能在電影院里將觀眾必須具備什么樣的知識作為前提去拍電影,如果這樣的話你的電影受眾太窄了。
比如謝晉導演,曾有人說他的作品過時了。但這一兩年,他在豆瓣里有好幾部作品突破了9分。這是因為他的故事講的好,故事里面講了人類的理想,講了人文的基本架構。這是歷史長河對本質問題的評價,本質問題歷史越長越看得清楚,相反時髦的東西都是短的,但時髦的東西也會改變一代人的風貌,這是我的經驗。
未來
AI將帶來翻天覆地變化,群體觀影需求無可替代
我對科幻是有一些好奇的。比如這一次平遙說到關于AI的討論,我的直覺告訴我,中國電影面臨了一次巨大的挑戰。就像在默片年代卓別林是至高無上的,所以有聲電影發明以后他拒絕拍攝。但替代是必然的,AI出現帶來的變化也是這樣。
我最近看了關于人工智能的書。在我的理解里,科學家已經給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定義,我們知道電腦程序會發出指令,這個詞告訴我們電腦是你的工具,但是在AI的面前,科學家說是對話,什么叫對話?智能之間的平等交融叫對話。我個人認為,AI不是工具而是交朋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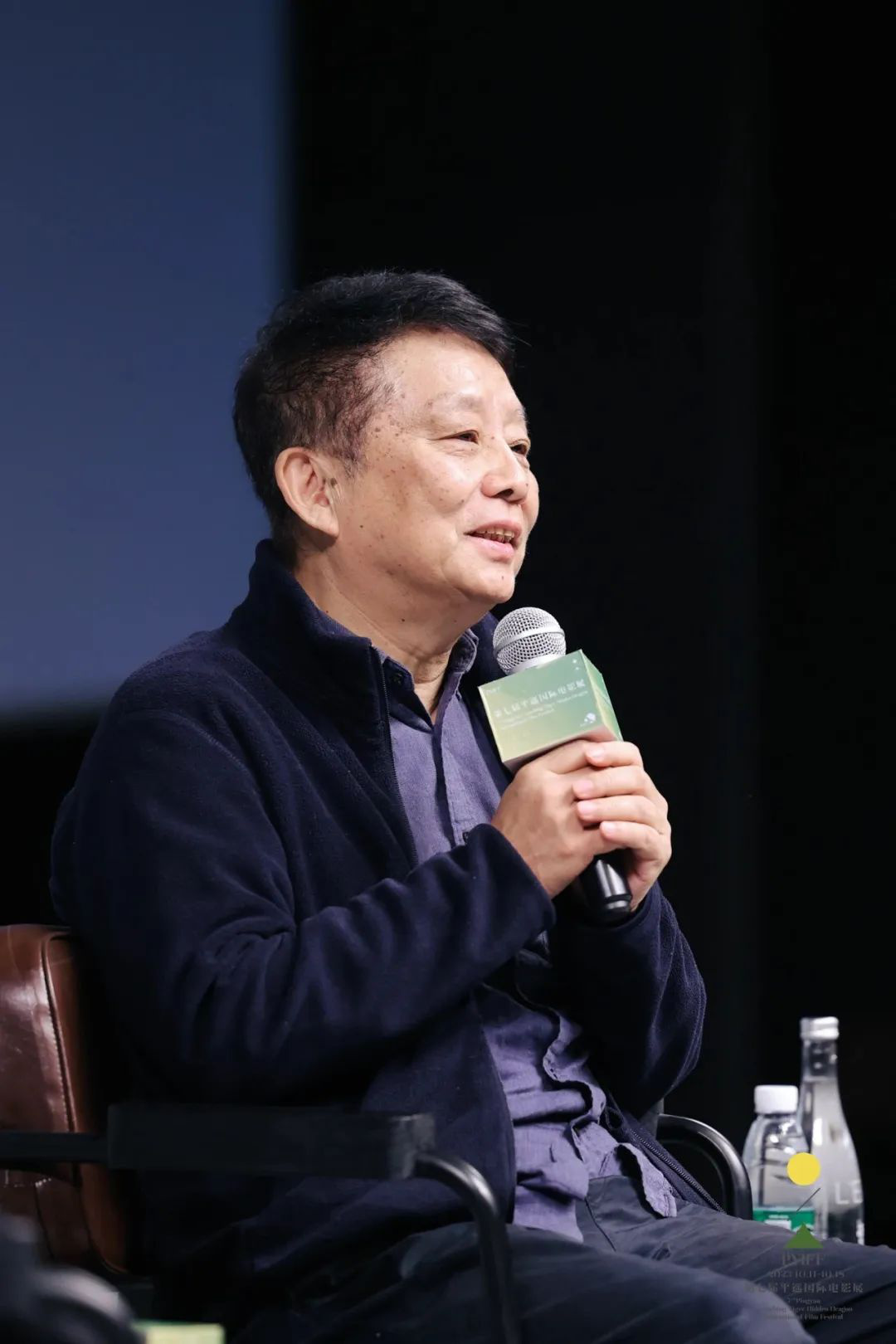
有科學家得出了所謂“篩子”理論:AI系統的閱讀速度和智商是人類的一千倍到一萬倍之間,假如它閱讀了賈樟柯導演的風格還有其他導演一千部、一萬部作品,或許它還無法出入自如,但在“過篩”后對內容進行重新儲藏和梳理,它的知識系統將是一個多人的綜合體。
AI還可能帶來什么樣的壓力?我看到了它在虛擬空間中的再造能力。未來,可能只需要幾個具有想象力的人加上技術保障團隊就可以和AI合作完成一部電影。從這個意義上講,AI會給電影帶來翻天覆地質的變化。
電影為什么比較敏感,因為電影和技術發展特別密切,全世界最先進的東西永遠都跟電影發生著關系。但觀眾(走進影院的)觀影需求是很難被替代的。場域里的情緒傳染就是電影的魅力,目前還沒有東西可以取代。


 凡人微光|重...
凡人微光|重... 如愿
如愿 微視頻|豐收新景
微視頻|豐收新景 青春華章|追光
青春華章|追光 豐收24小時
豐收24小時 青春華章·億縷...
青春華章·億縷... 聚一起 就是家
聚一起 就是家 億縷陽光丨被...
億縷陽光丨被... 微視頻丨同行...
微視頻丨同行... 土耳其水拓畫...
土耳其水拓畫... 新華全媒+|來...
新華全媒+|來... “中國歷代繪...
“中國歷代繪... 烏魯木齊“熱...
烏魯木齊“熱... 松花江哈爾濱...
松花江哈爾濱... 我國成功發射...
我國成功發射... 產教融合促就業
產教融合促就業 北京市民快樂...
北京市民快樂...